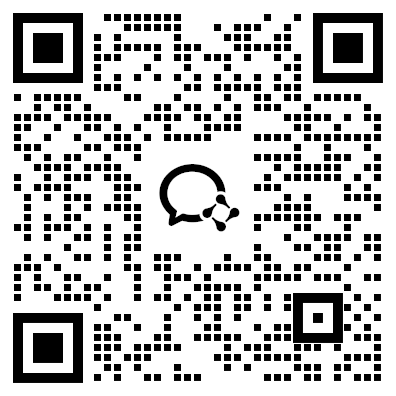共计 2825 个字符,预计需要花费 8 分钟才能阅读完成。
在游人排椅的前面行人路上,有一排街头艺术家给游人画肖像、漫画肖像的四五个摊子。每个画家有个自己坐的折叠小马扎,很窄,对面给画像客人坐的是比他们的大一点儿还有舒服的垫子的矮椅子。画家各自的距离是一个跟沙发一样长、半人高的铁架子(可以折叠,为的是方便搬运),架子上面用大夹子夹着各自素描的名人头像画,有半开大报纸那么大,白底画面,外加两寸宽的黑硬纸框。大概全世界的大城市里都有这种服务,中国的是毛笔字画,这里的是炭笔,在巴黎街头,我看到过用水彩的。这一排摊子里有一个正在用芭蕉叶编织小鸟虫鱼的中年女人,她前面的那个用两个纸盒子垛起来当展示桌的上面铺了一块印有“中国民航”的大蓝方巾,那上面摆满了青绿色、浅棕色的小玩意儿——青蛙、蜻蜓、知了、蝈蝈,大一点儿的还有鼠、龙、蛇、狗、鸡、猪……她手上正编织一条龙的爪子,这条龙是从头开始的,那上面已经有了两只眼睛和龙须。
没客人的时候他们四五个人互相聊天,一个人坐着、一两个站着。这几个来自中国大陆,说的是地道的北京话。其中一个朝我坐着的方向看了一眼,正好抓住我朝他们照相,这个大高个是个正面。他走过来,我有一霎间想到:“他不会要我把照片删掉吧(就像明星痛恨狗仔队那样)?”我坐在游椅上,他站着。“画一张吧!”很抑扬顿挫的北京腔,“对不起,不……”“算你十块钱?”他们的牌子上写的是二十块钱画一张,“嗯,对不起,还是不……”他转过头走了。当他用英文招揽不远处坐着休息的人,我才反应过来刚刚我们都用的是中文。
在街头讨生活的人没有那么多耐心,特别不喜欢不肯花钱又爱东问西问猎奇或者拍照的游客。你当他是你回家说故事的对象,他却日复一日、没早没晚,在寒风酷暑下坐在街头作画为的是挣钱糊口养家,有些人的心离那些闲情逸事很远。如果真想知道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做不到,你最好坐在那里、让他慢慢地画你,他才有心情跟你说话。你带走的故事大多数也是靠不住的,哪里有这幺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博士生在街头作画?怎么你就这幺幸运今天碰到一个?何况他给你画的那幅画仅仅像你老婆的舅舅。
看他们聊天画画。这情景是那么熟悉,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初来纽约上大学打零工的时候,在曼哈顿上班。早点儿晚点儿的时候就跑去看在旅游景点为游人画像的朋友,陪他们画画聊天。我认识两位从浙江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画家——章学林和陈达荣,他们在中国的时就已经工作了,一个搞舞台美术、一个在出版社搞插图。两个人都结婚了,只身移民来美国闯江湖,把孩子老婆留在国内。有了责任就不能不想养家糊口的问题,章老师陈老师在我工作的学校教绘画,选的是教晚上的课,零工性质的,钱很少,不过他们可以在那里免费学英文,与他们的学生练习英文口语会话,白天时候这两位摇身一变成了曼哈顿旅游景点街头画人物肖像的艺人了。他们傍晚来学校教课或者上课的时候拉着一个旅行箱,那里面放置着画像用的马扎、画纸、画架子、炭笔盒……那些挣饭钱的行当,那是他俩为了不占教室的地方特意买的。他俩合租一个公寓,什么东西都合伙用。
我那时白天上学,只好周一到周五做每天两小时记记账、发发工资的财务的事情,周末两天每天教四个小时中文,也是零工,钱很少。不过我图的是那所学校交通方便、工作完以后可以用个大教室做我的功课、不懂英文的时候一张嘴就可以问我的同行——英文老师……零工和全职不同的地方除了薪水少以外还没有休假、医疗保险等福利,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过渡时期管不了那么多,何况我还是个打黑工的。我没有绿卡、不能合法地工作,我上司担着很大的干系,天天提心吊胆害怕被税务局抓,可是又没办法让我滚蛋(我是他的老板给安插进来的)。我的上司嘱咐我不可以告诉任何人:“连你老妈都不能告诉……”“没问题!”我老妈在中国,她以为我在天堂呢,我只报喜不报忧。怎么能在靠讲究信誉才能生存的学校找到工作的呀?你问。那是另外一个幸运的故事。我告诉过你,我这个人真的很幸运。
有时周末天气不好不能在街头画像的时候,两位被风吹日晒黝黑脸膛的老师就跑到学校来。学校里有个小厨房,他们热热还没来得及吃的中午饭、喝免费的速溶咖啡和瓶装水,吃饱喝足了,抹抹脸叹声“今天没被抓。”旅游旺季的时候,主要景点像中央公园、时报广场、帝国大厦、格林威治村等街上有很多艺人,不仅有画像的,还有表演各种绝活的艺人,在窄小的街道上画的、被画的、唱跳的、跟着唱跳的、围观的……挤得让行人不方便过往,特别是晚上,自制的电灯上连着的电线常常绊倒小孩老人,时常有吵架的事情发生。有人向城管抱怨,城管和警察就常常到那些景点光顾,先是城管的人来过来告诉他们离开,过一会儿警察就走过来,如果还不走的话,再下来就是警车过来、偶然地拉一下警笛——这时候你就绝对要卷包走人,不然的话你的东西就进了警车、还要去警察局把东西取出来。都不是很贵的东西,可那是吃饭的家伙,所以得留着。他们浪费不起一天时间去领取,所以看到城管来了就开始打包、警察来了就离开,过两条街小马扎一打开又开张了……这样一个晚上换一个地方还行,有时跑的次数太多了,就不干了。好玩儿的是那些被画了一半儿的大人孩子还跟着这个作画的一起跑、过几条街摆个摊接着画、画完给了钱才高高兴兴地离开。
如果我没课或者分配坐办公室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就在一起聊天,无非是如何赚多一点儿钱、怎么省钱过日子——他俩有家要养、我要交学费,大家都很穷,钱的话题占了我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他俩那时异想天开地想在冬天去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街头作画赚钱的办法,我们越说越兴奋。很多北方人冬天都跑到阳光灿烂的迈阿密避寒,那里也是个冬天观光的地方,人很多。在纽约的街头冬天画画很冷,游人也不肯坐下挨冻,“生意不好,”他俩说。记得说到去迈阿密,我们的眼睛都闪闪发光!向往啊!
有时候周末下午每个班都没有课,全学校就是我们的了。那时候两位画家就切磋他们的素描技巧,我是他们的目标。几个小时下来,两人的素描本子里密密麻麻很多页都是我的鼻子、眼睛、耳朵、嘴巴、脖颈、肩、手指、手臂、头发、脚、鞋子、衣服……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完整的我。他们说“给你画张大油画”、自己去买油画布,我才不干呢,自己照照镜子就行了,谁花钱看自己啊,算了吧。我有时剪下来他们画的东西粘在一张画纸上,就成了卡通片的我。有一次我把小几号的眼睛弄成一排粘在额头上,很好笑很古怪的拼图,看起来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感动。后来陈达荣还是送给我一张完整的肖像,不是在我面前画的,他在家里画了一幅大一点儿的。他说画了那么多我的鼻子眼睛的,早记住我什么样子了。“想想你哪里都瘦、就是眼睛胖,就画出来了。”我那时只有47公斤,很多人以为我是越南难民。
多少年过去了,大家各奔前程,失去了音信。不知道两位老兄在美国还是回中国了?
夏日薰风从公园的树林、草地、花坛溢出,飘过广场上空顺便挽上马蹄哒哒、童声笑语,空气中缭绕着透明的情思。二十多年前那些仲夏静谧的下午,炭笔在纸上沙沙做响的声音……